
張恨水,祖籍安徽潛山縣。生于江西廣信,章回小說代表作家。
張恨水自幼酷愛文學,17歲就以“恨水”的筆名投稿,早期作品多為鴛鴦蝴蝶派言情之作。1924年,張恨水憑借章回小說《春明外史》一舉成名。此后,長篇小說《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的問世讓張恨水的聲望達到頂峰。
20世紀30年代初,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社會矛盾加劇,張恨水開始寫作以抵御外侮為主旨的抗日小說。
他一生創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小說,寫盡民國百態,老舍稱他“婦孺皆知”,茅盾贊他“為章回體續命”,他對舊章回小說進行了革新,把中國的章回體小說提高到一個雅俗共賞的新階段。
無論你之前是否熟悉張恨水的作品,都可以通過本期書單重溫經典,聽一聽極具特色的中國故事,感受中國章回小說的獨特魅力。
作品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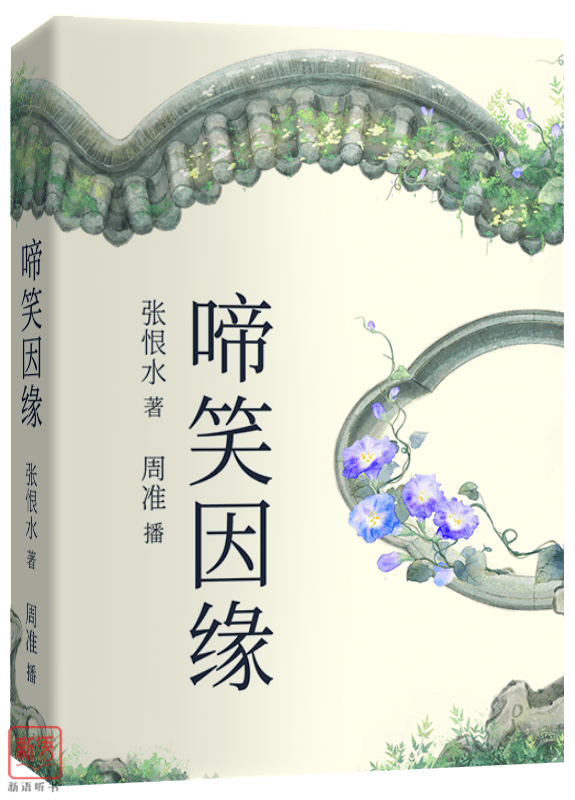
1929年,張恨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啼笑因緣》,并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
“言情”是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近現代通俗小說的重要特征。張恨水在《啼笑因緣》中開始嘗試“言情+武俠”的融合敘事,反響奇佳,以致當時商人登廣告,都要求報紙登在靠近《啼笑因緣》的版面上。此后,《啼笑因緣》風靡海內外,被認為是中國現代通俗小說里程碑之作,入選《亞洲周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
民國時期,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樹,在熱鬧的北京城中,先后結識了三位性格迥異、各有特色的女子:豪爽的江湖俠女關秀姑、天橋唱大鼓的姑娘沈鳳喜、富家千金何麗娜。由此展開了一段曲折離奇,卻又富有傳奇色彩的動人愛情故事。作者運用各種手法,安排了一連串巧合與誤會,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讓讀者看了上一回,猜不到下一回。
《啼笑因緣》內容通俗易懂,情感自然流露,在描寫浪漫愛情的同時,揭示了現實的殘酷無情,反映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社會生活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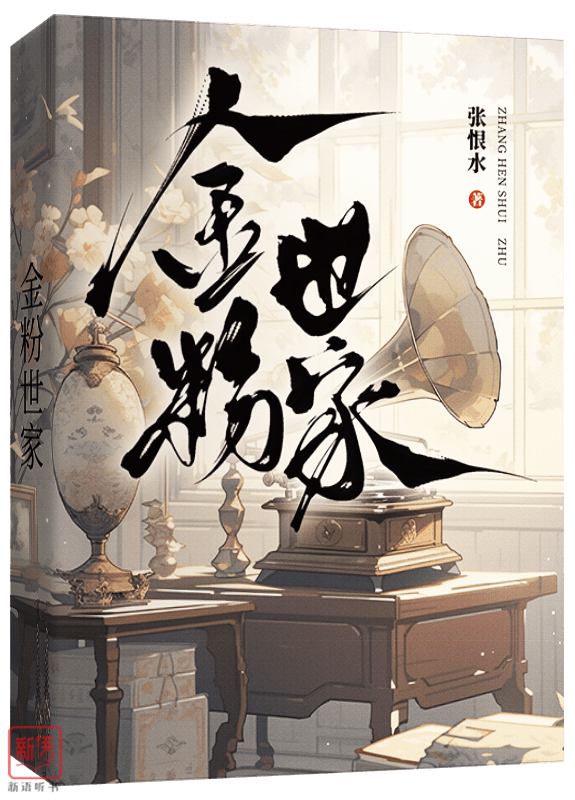
在中國小說史上,張恨水是一位非常特別的作家。
他能同時創作七部小說,創下同行最高紀錄。他的小說在報刊連載時便十分受歡迎,絕大多數都出版了單行本,魯迅都買了他的《金粉世家》和《美人恩》寄給母親看。
《金粉世家》是張恨水早期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1927年開始連載于《世界日報》副刊《明珠》上,全書共112回,約一百萬字。
小說以豪門少爺金燕西與平民之女冷清秋的愛情為引,描繪了一幅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風情畫卷。當冷清秋還是一個女學生時,金燕西不遺余力的追求使她怦然心動,但她又因為門不當戶不對,時時處于擔憂之中。小說通過兩人從戀愛到結婚,最后反目成仇的經歷,精彩地描繪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豪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實質,并且向讀者暗示,這樣腐朽的家族,走向崩潰是必然的。
“那時以為穿好衣服,吃好飲食,住好房屋,以至于坐汽車,多用仆人,這就是幸福。而今樣樣都嘗遍了,又有多大意思?”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范伯群曾評價此書說,“《金粉世家》才是張恨水的代表作,是他的百十部小說之巔”。如果你想了解張恨水,一定要讀讀這本《金粉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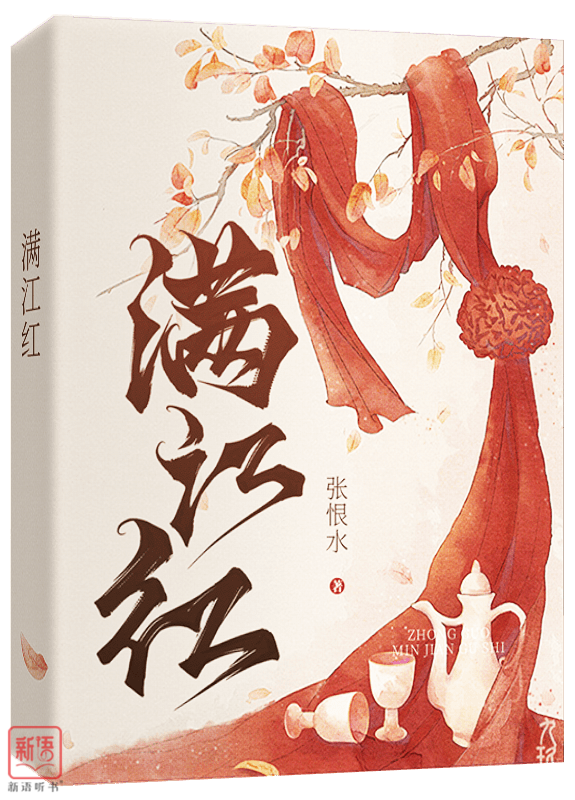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必定伴隨著舊事物的衰亡和新事物的成長。在中國現代小說觀念的演變過程中,章回體一直被視為“舊形式”,被批判、改造。
但張恨水卻說:“我覺得章回小說,不盡是可遺棄的東西,不然,《紅樓》、《水滸》何以成為世界名著呢?”
他在吸收傳統文化精髓的同時,大膽借鑒外國小說的一些表現手法,比如場面描寫、內心獨白等,創作了大量經典作品。
《滿江紅》講述一位年輕有為的畫家于水村因偶然的機會結識了秦淮河畔歌女桃枝,兩人陷入熱戀,卻因誤會導致分手。桃枝賭氣答應另嫁他人,婚禮上,不能忘情的桃枝追著酒醉的水村上了船,恰逢渡船起火,桃枝救下爛醉如泥的水村,自己卻被燒死在火中。得救后的水村沉浸在傷痛中不能自拔,偶然看到歌舞劇《滿江紅》,講的正是一女與情郎易裝救人的故事,遂逐夜追看,緬懷與桃枝的感情,終于因傷痛過度,在抑郁中死去。
張恨水以細膩的筆觸,將男女主角的心理活動描繪得生動而真實,通過對歌女悲劇命運的描寫,揭示了當時社會的貧富懸殊、階級壓迫以及對人性的扭曲,為讀者呈現了一幅民國社會的人生圖景。

抗日戰爭后期,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惡性膨脹,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夜之間,黃金從每兩法幣2萬元提高為3.5萬元,上漲75%。獲知內幕消息的達官顯貴們連夜搶購黃金,轉手即獲厚利。
《紙醉金迷》就是以此為背景創作的,原載于1946年上海《新聞報》,是張恨水后期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
小說以抗戰勝利前夕的陪都重慶為舞臺,以一個漂亮虛榮的女學生田佩芝的沉淪史為主線,描寫了重慶從政壇到商場,從上流到底層,人人都陷入倒賣黃金、炒作債券的金融漩渦中。
書中童謠唱到,"買黃金,買黃金,瘋了大重慶。家事不在意,國事不關心,個個想黃金,個個說黃金,有了黃金萬事足,黃金瘋了大重慶。"
官吏大發“國難財”,商人大做“黃金夢”,小市民“紙醉金迷”,無人不做著一夜暴富的美夢。人性、感情、靈魂、肉體都成了投機和賭博的砝碼。最終不僅輸掉了家庭和愛情,還輸掉了自己的良知和尊嚴。
《紙醉金迷》講述了大時代背景下的世態炎涼,以及人性在金錢面前的迷失與掙扎,它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